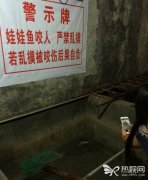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,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。我死后当草草棺殓,即行藁葬于清华墓地。汝等不能南归,亦可暂于城内居住。汝兄亦不必奔丧,因道路不通,渠又不曾出门故也。书籍可托陈、吴二先生处理。家人自有料理,必不至不能南归。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,然苟能谨慎勤俭,亦必不致饿死也。五月初二日。父字。
父亲的后事
这份遗书是父亲自沉(阴历五月初三日)的前一晚写的。据母亲说,他当晚熟睡如常,并无异样,可见他十分镇静,死志早决。
依了父亲的意思,我们不曾请风水师择坟,也没挑选“吉日”,就在清华外面七间房买一块地把父亲葬了。坟是清华的泥水匠做的,立了一个碑,上书宣统皇帝封的谥号“王忠慤公”,坟地四面都种了树。
“王忠慤公”是有一段来历的。父亲去世之后,罗振玉先生送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父亲的“遗折”给皇帝,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。宣统皇帝读了大受感动,和师傅们商量后,发一道“上谕”为父亲加谥“忠慤”,派贝子溥忻前往奠醊,赏陀罗经被并大洋两千元。
“遗折”是罗先生命他的第四子仿父亲的字迹写成的。罗振玉先生为什么这样做?想是要利用父亲“忠于清室”来标榜自己吧!
这些年来,凡是有关父亲的任何资料我都尽量剪存并仔细阅读。时间越是长远,越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父亲的感情与愧疚,正如父亲的词句:“已恨年华留不住,争知恨里年华去。”(〈蝶恋花〉之五)
三哥说,想到父亲生前:“往往以沉重之心情,不得已之笔墨,透露宇宙悠悠、人生飘忽、悲欢无据之意境,亦即无可免之悲剧”之情境,总会怆然而泪下。
母亲遭打击
父亲突然去世,为家中笼罩了一层愁云惨雾,每个人都食不下咽,即连佣人亦不例外。由于母亲无心料理三餐,家中当时常不举炊,每天从“高等科”厨房送来两餐包饭,大家却是略动筷子,即照原样收回去。后来由钱妈把家事接下来,又开始每日由成府小店送来预约的各种菜蔬,再行自炊。
母亲那时每天都到成府刚秉庙,为父亲棺木油漆督工。那时用的并非现在用的快干洋漆,而是广漆,每一层必须等待干燥后,才能再漆,费时不少。漆了几次后,外面加包粗麻布,再漆,再包,共七层之多,然后再加漆四五次,到后来,其亮如镜,光可鉴人。当时正处盛夏,辛苦奔波还在其次,最难耐的是庙中隔室另有一具棺木,是早些时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中被枪杀的一名清华学生。因棺木太薄,又未妥善处理,远远就闻到阵阵尸臭,母亲亦未以为苦。
接着购地,挖掘坟穴,也是她在忙着。钱妈悄悄地对我说,让她去忙,这样可稍减悲痛的心情。
有一天下午,母亲又到坟地看工人修筑墓穴去了,家中别无他人。我因要找东西,请钱妈帮我抬箱子。抬下第一只,看见箱面上有一封信,是母亲的笔迹,上面写着我的名字。当时我立刻联想到从父亲衣袋中取出来的遗书,马上感到一阵心跳手抖,知道不是好兆。好不容易把书信打开来一看,是母亲的遗书!
信中大致是叫我们把父亲和她安葬以后,即筹划南归,回到家乡去依靠舅父及姨母生活。父亲的抚恤金,清华原定每月照付薪金到一年为期,由三哥按月领了汇给二哥管理,合并其他的钱,勉强够我们的生活教养费。
这突如其来的事情,对一个不足14岁的孩子来说,简直不知所措。幸亏钱妈比我冷静沉着,叫我不要声张,即使是家人面前也不要提。
她问我与母亲较好的有哪几位太太。我说和西院1号陈伯母(陈达教授的太太)、4号郑伯母(郑桐荪教授的太太)和南院赵伯母(赵元任教授的太太)三人比较接近。
我和钱妈商量一下,觉得陈伯母太老实,不善言词,恐怕说不动母亲,无法让她改变心意。赵伯母心直口快,将来说漏了嘴,全园皆知,是很尴尬的事。只有郑伯母说话有条理,行事很谨慎,且与母亲最谈得来,因此马上去与郑伯母商量。
郑伯母叫我不要惊慌,说她一定尽力说服母亲,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分上,多管我们几年。然后在家中,由我哀求,钱妈劝解,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。母亲说了一句:“好吧!我再管你们十年。”我才如释重负放下了大半个心。
父亲轻生之谜
对于先父王国维之死,已断断续续地议论了半个多世纪,究竟孰是孰非,一时尚难下断语。最近因罗振玉先生的长孙罗继祖所编《永丰乡人行年录》(即罗振玉年谱)问世,以及先父在大哥逝世后为大哥海关恤金事给罗的三封信,由罗继祖发表,流传海外,学者又开始留意对王、罗失欢原因的追究。
看了1984年9月30日台湾《中国时报》副刊上杨君实先生的《王国维自沉之谜后记》后,觉得他的观点与论点,值得商榷。
所谓“百思不解”的谜底,杨氏摘录的《永丰乡人行年录》中的一段,说是已原原本本地道出来了。其要点为:潜明、高明、贞明为静安元配莫出,潘为继母。长媳与继姑不睦。家政皆潘主之。潘处善后或有失当。孝纯诉之于父,父迁怒静安听信妇言,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,遽携女大归。罗令女拒收海关恤金。以上各点,隐示王、罗的失欢皆归咎于继姑潘氏。杨文末所引先父与罗氏的信,乃民国6年(1917年)张勋复辟失败后所写,未加指明,颇觉突如其来。
杨先生认为罗继祖原原本本说出来的为长媳与继姑不睦为主因,治丧或失当为导火线。而事实上是否如此呢?在此必须一辨。
大嫂在民国7年(1918年)17岁时,就嫁过来了(杨文误作辛亥东渡时)。至民国15年(1926年)大哥病故,仅有七年多,小部分时间与翁姑同住,其他时间,有住在天津娘家的(当时大哥调职天津海关),亦有小家庭独住的(大哥调回上海海关以后)。姑媳相聚之时确是不长。
在大家庭中,姑媳意见偶有相左,亦是常事,何致像火药库一般,一引导火线即爆发呢?在罗举家徙居东北以前,婆媳之间时有书信往返。犹记民国18、19年(1929、1930年)间,大嫂曾由津赴沪,并返回海宁探视先母。民国37年(1948年)冬,托人带信给母亲,欲随母亲同住。
如果与继姑心存芥蒂,平日又何必书信存问,又何必绕道省视?母亲为人继姑者,并非长媳一人,对二三两媳亦属继姑身份。可是她们相聚很久,婆媳之间都很融洽,情如母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