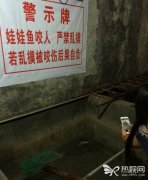(九月十九日)
第三封:
昨奉手书,敬悉种种。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嫒之名存放,否则照旧日银庄之例用“王在记”(按大哥又字在山)亦无不可。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嫒之物,不容有他种议论,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,其间恩义未尝不笃,即令不满于舅姑,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,何以于其遗款如此拒绝。若云退让,则正让所不当让,以当受者不受,又何以处不当受者,是蔑视他人人格也,蔑视他人人格,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。总之,此事于情于理皆说不过去,求公再以大义喻之。
(九月二十五日)
以上三信,先父在沉痛中,用笔仍委婉恳切,尚期异日再见,毫无绝情之意。经过一再恳求,大嫂才把遗款收下了。
罗继祖在《观堂书札》再跋里,曾提及有人在他父亲(罗振玉长子福成)处,见到先父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,写在八张八行纸上。其中谈到叶德辉(清代御史,著名藏书家,出版家)的死,具体怎么说,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。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,十年动乱中,听说已佚失。这封信,罗继祖并未看到,他估计当时久未通信,很可能是先父为叶德辉事,破例去信示警的,而他家未敢以呈罗,致保存在他父亲遗箧中。由此可见,先父为人的敦厚与怀旧之情的殷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