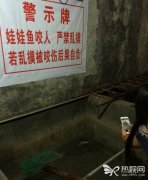说到治丧事件,当初共同办理丧事的,尚有二哥高明,时年25,三哥贞明,时年22,及老佣人冯友。早已成年的二哥、三哥都是大哥的同母弟,当无偏颇情事。先父平日除研究学问外,很少管日常事务,现遭丧子之痛,心情恶劣是可想而知的。枝节小事,家人不敢再去烦他神,治丧事宜由母亲代劳是可信的。
至于罗继祖文中说“潘处善后或有失当”,乃属臆测之词,究竟什么地方什么事失当?未能指明,而用“或”字约言之。我无意说他而为乃姑及乃祖辩护,但臆测之词,是不足证明过去事实真相的,而徒使无辜者遭受不白之冤。
我在《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》一文中,尽可能避免用类似口吻,来假定大嫂方面的因素。一则不愿有损大嫂清誉,她曾是大哥的爱侣,大哥早死,连子女都没有留下,命运的坎坷,已经够可怜了,何忍再加以议论!再则恐有为先母辩白之嫌,不知者或讥为“女为母隐”。因此用百思不解一词,一笔带过。
这次事件的发生,毋宁说是偶发事件较为合理,因事先并无失和迹象。其时父亲丧子,大嫂丧夫,都是在哀痛过度的时候,而罗氏为爱女遭遇不幸,舐犊情深,心中自亦不好受。
当此情景,每人情绪都很激动,任何小问题,若稍有歧见,大家都无好言语,小误会成了大争执,以致不可收拾,罗氏一怒携女大归。其实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,大哥过世时,大嫂才24岁,可以说心智尚未十分成熟,在顿失依靠的时候,既无儿女可守,那么最可信赖的,当然是父母。像大嫂这样遭逢不幸者,多数人都会选择返回父母跟前之一途。至于大嫂当初是否本有归宁之意,或因误会而临时动意随父而去,则不敢妄下断语。
东明当时年幼,不敢过问大人们的事,其间隐情,实难了解。不过就常理言,大哥亦由先母带大,大嫂又是罗氏的掌上明珠,以两家关系之深、情谊之厚,先父母绝对不会不尊重大嫂的意见。只是个人的感受不同,新寡的大嫂,心理上总是饱受委屈的,乃向她父亲诉起苦来,罗氏听后便心中不平了。所谓大归,只是罗家的说法,我们王家并无此说,兄弟姊妹仍视孝纯为我们的大嫂,是家中的一员。
先父性情敦厚,怀旧之情殷笃,虽在沉痛中,用笔仍委婉恳切,毫无绝情之意。先母主理家政,非自为姑之日始,先父当年续弦的主要目的,即为支持门户(见王德毅编《王国维年谱》,48页)。先父这一生中,如无两位母亲先后为他处理家务,无内顾忧,恐怕不会有那么辉煌的成就。
有关大嫂拒绝领受大哥海关恤金事,罗继祖于1982年8月发表跋《观堂书札》于《读书》上,引录三封先父给罗氏劝大嫂勿拒收恤金的信,兹摘录于后:
第一封:
维以不德,天降鞠凶,遂有上月之变,于维为冢子,于公为爱婿,哀死宁生,父母之心,彼此所同。不图中途乃生误会,然此误会,久之自释,故维初十日晚过津,亦遂不复相诣,留为异日相见之地,言之惘惘!初八日在沪,曾托颂清兄以亡儿遗款汇公处,求公代令嫒经理。今得其来函,已将银数改作洋银二千四百二十三元汇津,目下当可收到。而令嫒前交来收用之款共五百七十六元,今由京大陆银行汇上,此款五百七十六元与前沪款共得三千元正,请公为之全权处置,因维于此等事向不熟悉,……亡儿在地下当为感激也。
(九月十八日)
第二封:
昨函甫发,而冯友回京,交到手书,敬悉一切。令嫒声明不用一钱,此实无理,试问亡男之款不归令嫒,又当归谁?仍请公以正理谕之。我辈皆老,而令嫒来日方长,正须储此款以作预备,此即海关发此款之本意。此中外古今人心所同,恐质之路人无不以此为然者也。京款送到后,请并沪款以并存放,将原折交与或暂代为收存,此事即此已了,并无首尾可言。